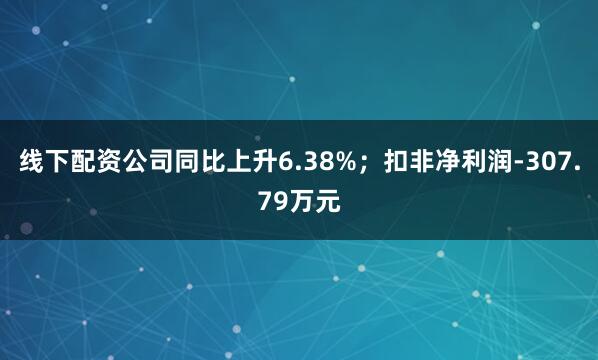1959 年 12 月 4 日,53 岁的溥仪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。那天雪下得不小,他手里紧紧攥着那纸特赦通知书,踩着没脚踝的雪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—— 这个曾三次坐上龙椅、又当了十年战犯的人,终于有了个新身份: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可这份 “新”,却让他心里没着没落的。
回京后,溥仪住在五妹金韫馨家。每天天不亮就醒,看着家里人忙忙碌碌,自己却无事可做。后来他索性对着镜子练系红领巾,手指笨拙地绕来绕去,总也系不整齐。这日子熬了两个月,他实在憋不住了,托人给周总理捎了句话:“我想找份工作,哪怕是扫大街也行。”

周总理早把他的心思看在眼里。1960 年春节前,中南海西花厅摆了桌家宴,溥仪揣着忐忑坐在总理对面,连夹菜的手都在抖。饭吃到一半,总理突然开口:“溥仪同志,以后想干点啥?” 这话一问,溥仪手里的筷子 “啪嗒” 一声,夹着的四喜丸子直接掉进了醋碟里。
他抹了把额头的汗,小声说:“我想学医,当大夫。” 溥仪说这话不是没底气 —— 小时候他总生病,太医院的老御医手把手教过他把脉开方;在战犯管理所那十年,他没事就翻《黄帝内经》,早就盘算着:要是能去医学院进修两年,说不定就能坐堂问诊,也算有门手艺。
可周总理听完却轻轻摆了摆手:“您这双手啊,适合拿笔杆子,不适合拿听诊器。” 溥仪愣了,直到后来才知道,总理早把他的情况摸得门儿清 —— 之前在管理所,他给狱友把脉,愣是把普通感冒说成 “风寒入体”,让人家连喝了三天浓姜汤,差点没脱水。更关键的是,以他 “末代皇帝” 的身份,万一哪天出了医疗事故,那可不是小事,是要牵动人心的历史性问题。

学医的路走不通,溥仪赶紧补了句:“那…… 要不让我回故宫当讲解员吧?” 这话一出口,桌上的亲戚都悄悄点头 —— 论对故宫的熟悉,谁能比得过在这儿住了二十多年的溥仪?他连乾清宫地砖上有几道裂纹都记得清清楚楚,那些藏在宫墙犄角旮旯里的秘闻,更是没人比他懂。
可周总理却端起茶杯,半天没吭声。溥仪心里直打鼓:这要求也过分吗?难道真要让我去扫大街?他不知道,总理此刻正在盘算:故宫每天上万游客,他往太和殿前一站,老百姓瞧见了,是该鞠躬还是不该鞠躬?更别说他当年做伪满洲国皇帝的事,万一有人记恨,扔个臭鸡蛋、烂菜叶,那该多难堪?
见溥仪急得直搓手,周总理笑着推过去一盘豌豆黄:“先尝尝这个,老北京的味儿。” 等溥仪吃完,总理才慢悠悠开口:“我看啊,您先去香山脚下的植物园,种种花养养草,挺好。”

溥仪当时还有点抵触:“我这双手,以前是给皇后梳头、握玉玺的,哪能干粗活?” 可没辙,他还是去了植物园。每天浇水、剪枝,累了就坐在葡萄架下晒太阳。没想到俩月后,他培育的月季竟在全市花展上拿了奖 —— 捧着奖状的那一刻,他忽然觉得,这比当年坐在龙椅上还踏实。
在植物园待满一年,组织又把他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委。这回溥仪可算找着了用武之地,整天抱着档案袋跑故宫、访遗老,把末代宫廷里的那些事儿一笔一划写下来。后来他写的《我的前半生》成了畅销书,光稿费就够在京城买套四合院。
1967 年溥仪去世时,身边的遗物除了几个药瓶子,就剩半本没写完的工作笔记。最后一页字迹有些潦草,写着:“今天给月季修枝,想起小时候在御花园…… 还是现在舒坦。”

六十年过去了,溥仪当年想干的两个职业,如今都成了 “香饽饽”—— 医学院分数线一年比一年高,故宫讲解员的录取率比考公务员还低;现在故宫还特意开了 “皇帝专线”,导游穿着龙袍讲历史,票价贵三倍还场场爆满。有人说,要是溥仪活到现在,说不定能成个网红讲解员。
可只有回头看才懂,当年周总理的两次拒绝,哪里是不给他机会?是怕他扛不住职业风险,怕他再卷入是非,是想让这个经历了三朝更迭的老人,能在花木扶疏里,安安稳稳过上不用向任何人下跪的日子 —— 这份藏在 “拒绝” 里的保护,比任何 “机会” 都珍贵。#最后一位皇帝溥仪#
盈昌配资-盈昌配资官网-配资查询网-在线股票配资配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